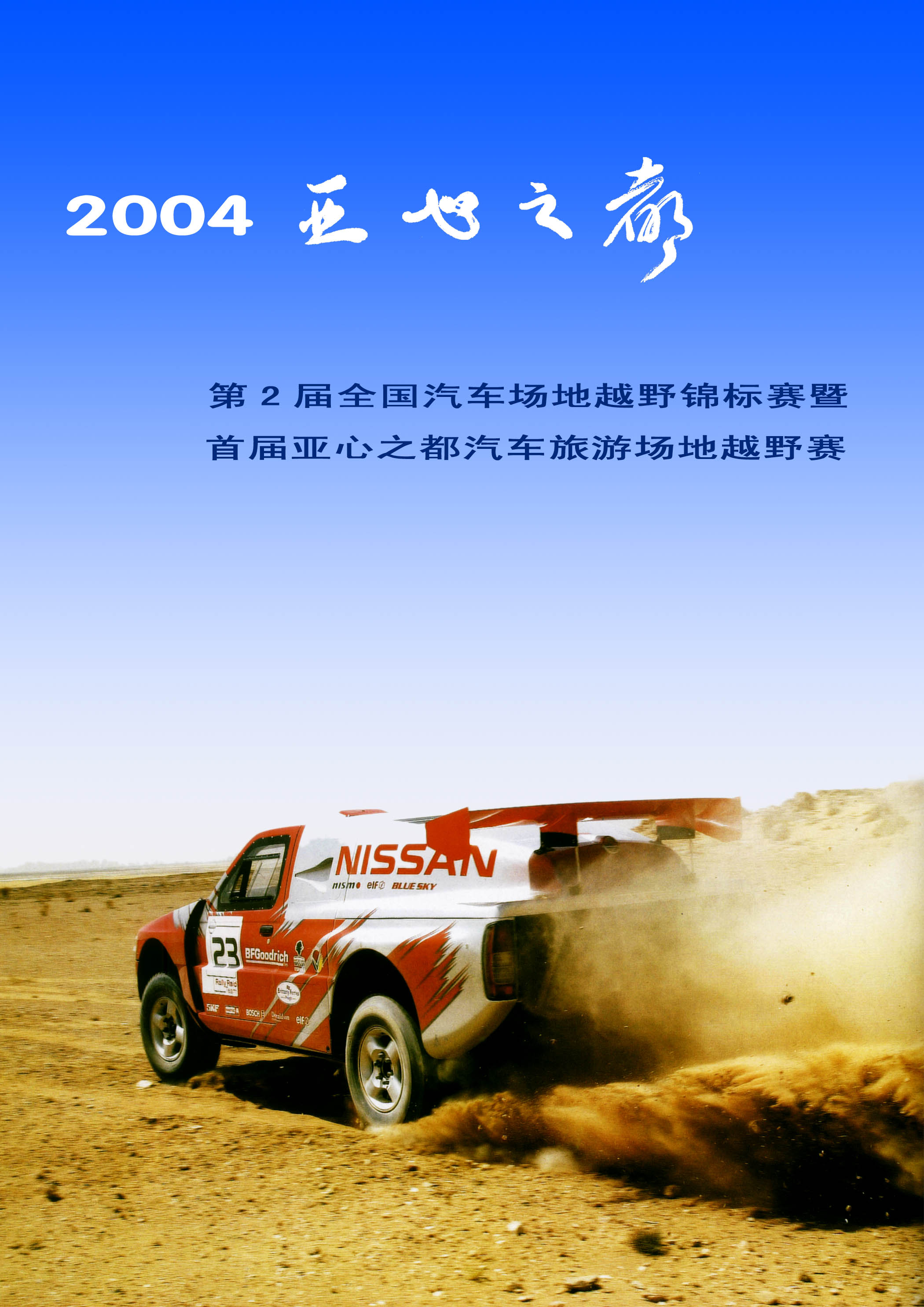七户人家的村庄
三毛/文
七户人家的村庄,镶嵌于翠绿的万亩旱田中,在一个叫平顶山的地方,有树、有牛羊、有年久失修的土胚房。而几户新建的砖瓦房又把我们从恍若隔世的时空拉回到现实。
村庄依坡势而筑,躲避着一种喧嚣,也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一方宁静,以免纷繁乱象的入侵。村庄的生存看似脆弱,却有根深蒂固的传承,镌刻在屋檐木板上的雕龙画凤,更像是述说一个古老的故事,在断断续续中长满了青苔。
村庄有城里人无法想象的一种静谧,好似人们厌倦了面面相觑的没话找话的尴尬,总想在内心敞开一扇对话的窗口,回到返璞归真的宁静。无疑,村庄成为了我们拥抱大自然和走向自然之子的纽带,我们暂且抛开了村庄本身所经历的艰辛苦难和曾经的贫瘠,放眼望去,是万亩旱田中绿油油的麦苗和鹰嘴豆苗茁壮成长的景象。
村庄犹如恬静的女子,婀娜款步、长袖起舞,撩动了树影婆娑的枝叶,也唤醒了沉睡的土地。斑驳的阳光总是在和风中温暖地抚慰我们的脸庞,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快乐,没有写在村庄的脸上,却深深印在了村庄的心里。我们突然的造访,我们在不知不觉的行走中,与七户人家的偶遇,这算不算我们生命中的另一个驿站?我们拼搏在瞬息万变的时代,穿梭于都市的人潮人海中,我们的疲惫和所谓的奋斗能不能在这里放缓脚步?做到一次真正物我两忘的心灵小憩。人在疾走如飞时,往往会错过风景。那就让我们在这个消化不良的社会和狼吞虎咽的物欲中,给自己一次慢咀细嚼的机会吧,亲近一下我们不能舍弃的村庄,就像从牛栏羊圈里鱼贯而出的四条腿们,“咩咩”“哞哞”地长哼短叫,比起人类两条腿的行走,更为漫不经心、悠闲自得,然后在主人那根长鞭的指引下,涌向草原,散落在漫山遍野的绿色中。
村庄寂然。
而我们怀着都市人的虔诚在诗意的寻找,总想在村庄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一种旷古的情怀,或者寻觅到徜徉于心的小桥流水、西风瘦马。没有任何的波澜起伏,村庄依旧,平凡得如同你我的故乡,只是你倚靠在断垣颓壁的土胚前,一种无以言表的乡愁汹涌而至,让你真切地触摸到了祖辈们男耕女织偏安一隅的微微心跳。
我们回来了,回到我们梦寐以求的村庄。
村庄没有古镇的模样,更没有江南村落青砖黑瓦的做派,譬如说宏村,让凌霄的飞檐固化成历史的记忆,譬如说西递,让孱弱的女子在沉重的贞节牌坊下徘徊流连。我们的村庄很简单,只有蝉鸣鸟欢,只有荷锄而过的寒暄,只有一张张耐寒耐旱的面孔,抵御一生里苦与乐的渐渐逼近的沧桑。这种沧桑在村庄肆意的蔓延,如割麦的镰刀,又如耕地的犁耙,沾满了泥土,也溢满了丰收的喜悦。
我们终于找到了乡村的灵魂,那是土地,质朴而厚实的土地,充满芬芳的泥腥味,在我们脚步千万次的聆听和叩问中,散发着淡淡的乡愁。这股乡愁,送我们进入了陌生的城市,这股乡愁生长在了我们心灵的故乡,尽管我们来到了眼前这阔别数载的并不属于我们的村寨,但它每一次的原始的呈现,它弥漫在空中的气味,都有故乡的影子,都记录了我们亿万个村庄基本生存的方式,于是我们在这个村庄的缩影里,回忆我们的童年,回忆我们的青春,并无限放大了我们与土地息息相关的亲密和不离不弃的厮守。
其实,我们就是行走的过客。我们的到来和告别,不会给七户人家的任何一人,带来大起大落的情感波动,更不会有依依不舍的离愁别绪,在我们四目相对里,只有平淡如水的日子,以及他们挂在脸上的真挚善良的微笑,然后留给我们一个似曾相识久违了的微微弯曲的背影,这就是村庄的脊梁,挑起了村庄的责任,也扛起了村庄的未来。
村庄的七户人家,看似如千千万万的农户一样,平淡无奇,而他们的举手投足和寡言少语的沉默里,又透着几份神秘、传奇,村庄的前世今生也笼罩在了一种庄严的气氛里。他们在西域的木垒默默耕耘,守护这万亩旱田。他们在祖辈尚武的铠甲下,蜕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村野农夫,并把这曾经的乱山荒地开垦成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
据说,他们最早落户于此的先人是清朝骁勇善战的清兵,为平定准噶尔叛乱,岳飞的21代孙岳忠琪奉朝廷之命,据守木垒。雍正10年,岳忠琪率全体将士及当地百姓,破土动工,建穆垒(木垒)县城,并大开阡陌,屯田垦地,沃野千里,良田无数。当时,有几个受轻伤的士兵想解甲归田留在木垒,岳忠琪即刻准允,并指着远方的平顶山说:“那里有万亩旱田,只要辛勤耕耘,定可丰衣足食。”从此,几个士兵在这里默默劳作,结婚生子,过上了真正的农家生活。
或许这只是一个传说,或许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当我们询问村人时,他们有的轻描淡写,仿佛祖辈的事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有的则郑重其事,认为有他们这样血战疆场的先辈,是一件无限荣光值得骄傲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村庄依旧平静,万亩旱田依旧悄然生长,他们依旧年复一年过着平凡而安静的日子。
我以此记之。还想续续村庄祖辈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