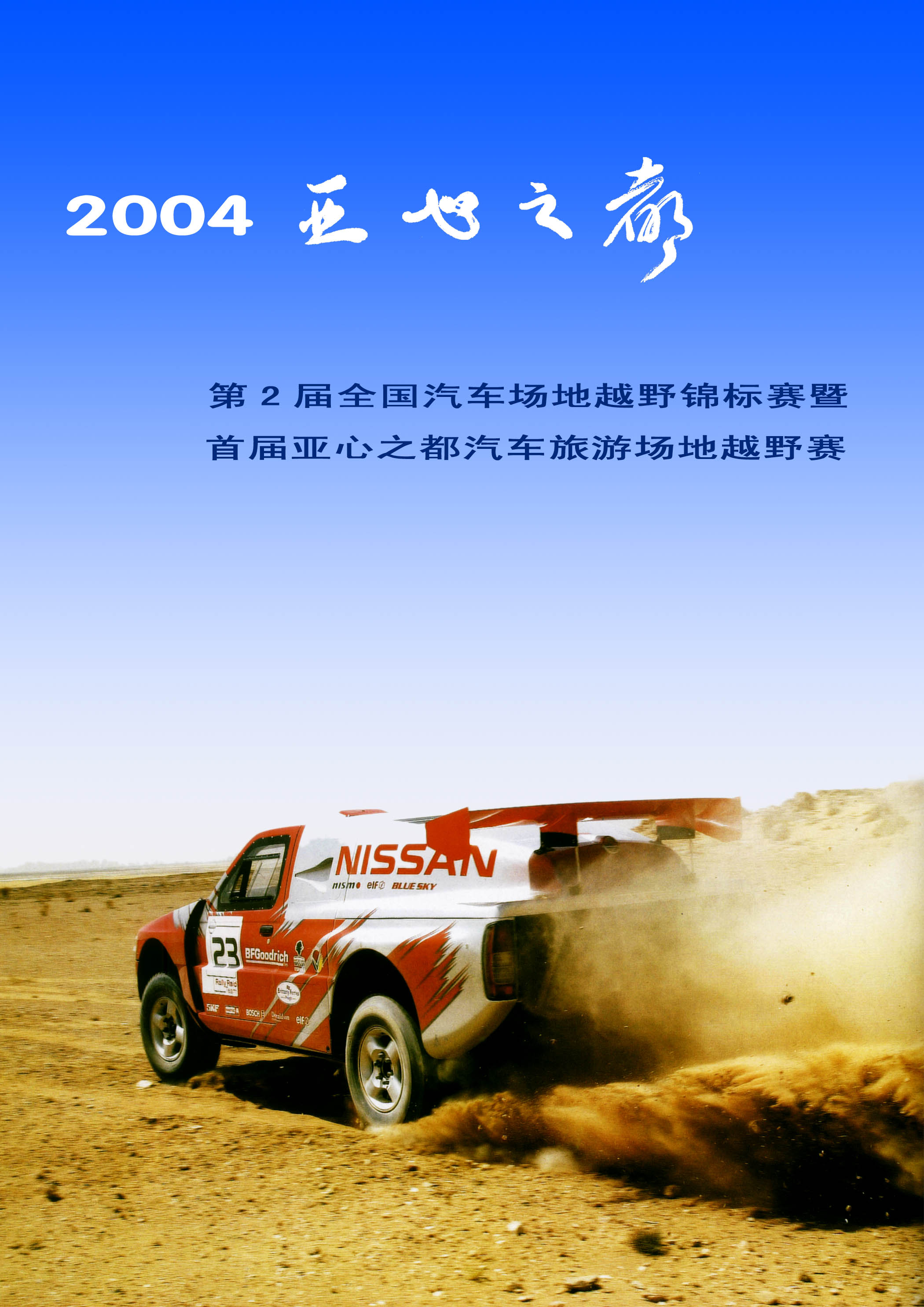旅游区的几个自然村落
三毛/文
千百年来,乡土社会孕育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土”字,“土”是生命之源,是文化再造和复兴的基础。
——费孝通
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
——梁漱溟
“清江一曲抱村流”,木垒河流域自然村落的各自环抱,形成了天山脚下最美的画面,也演绎着农牧交错地带独具木垒风味的乡村生活。
这里盛产小麦、豌豆、鹰嘴豆,被誉为“西域粮仓”,大片大片的种植地铺展在照壁山舒缓的土坡上,犹如东天山织出的柔软绸缎,包裹着温暖的乡村。
河台子村,迷宫一样的村落,阡陌纵横,步入其中,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奇神秘,寂静中传来隐隐的鸡鸣狗吠,把我们带入一种亘古的中国式的农家田园之境。绿油油的菜畦庭院,炊烟袅袅的麦秸柴火的香味,深居于此,游人淡淡的乡愁油然而生,更加向往这种“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乡村生活。
旅游区的每一个村落都散发乡村原始的气息,淳朴而自然、静谧而恬淡,但它们又呈现别具一格的姿态,彰显着村落生存状态的丰富多彩。
河坝沿村,是自治区首批授予的“传统村落”,它完整的保留了传统民居的乡村建筑。走进村落,既有一种怀旧又有一种乡村血脉相传的诗意。上百年的老房子在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中依然保存完好,巴郎房矗立的梁木依然坚硬如初,经受着岁月的洗礼。用两个字形容河坝沿村的特点就是“古老”。相传村落的祖辈大多从陕甘宁一带走西口到了照壁山乡,他们也带来了中原地带的农耕文化习俗,口耳相传至今,即便是现在村落后人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新疆人,但在这个农牧交错地带仍旧留存了汉文化农耕习俗的因子,并很好地与当地哈萨克游牧文化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充满地域特色的“雨养旱作”农业文化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它的“古老”,在于它建筑风格的古朴、民居的自然环境的讲究、以及和谐相处老幼有序的乡村生活;它的“老态”也是河坝沿村的一种农耕延续,村子山坡田畴中的老杏树已经长到了两百多岁,依然在以顽强的生命力,孤独的守望麦田。村里80岁长者刘老爹说:“这是他爷爷的爷爷种下的,老杏树也在保佑我们刘家大院的人丁兴旺。”在他小儿子刘永学的家里,典型的巴郎房,麦场和屋檐下摆满了老物件:割麦的钐镰、打麦的木板、碾麦的石磙,老农具样样齐全。刘永学擅长说唱,为人活跃,传承了爷爷的那些老曲子,也叫“新疆曲子”,里面融合了许多民族的韵味,却又带着浓浓的陕甘宁的民歌味,还有“花儿”调,也有哈萨克民歌的苍劲辽远,几种调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刘氏”的独特唱法,也算得上民间高人。河坝沿村正因为有了这些“古老”的习俗和民居生活,我们从村落的建筑和老物件中,看到了他们精神生活中对中国乡村文化一种坚守和传承的乐观态度。
平顶山村,当地人一般都叫它“下泉子”,意思就是“多沟多泉”,湿地密布。村落静卧于连绵起伏的万亩旱田麦浪中,50多户人家,也算是照壁山乡最繁华热闹的村庄了。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在“雨养旱作”的农业生态自然环境下,也练就了乐天知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情趣,上天眷顾于他们,带来了色彩与美,也带来了五谷丰登。即使遇到干旱之年,这里仍旧是一派丰收祥和的景象,因为这里溢出的小溪沟泉,就像母亲的乳汁滋润大地。当地流传着一句谚语:瞎了戈壁滩,肥了平顶山。有再大的干旱,东天山下的这块风水宝地,依旧万物葱茏,生机勃勃。平顶山的春夏秋冬,四季如画,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画家和作家们在此创作、体验生活。雨养旱作的农业文明,给这里的乡村生活带来了无限诗情画意,人在画中,心在陶醉,古朴的村落与唯美的画面,勾勒出了“白云深处有人家”的中国农耕乡村真实生活的生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