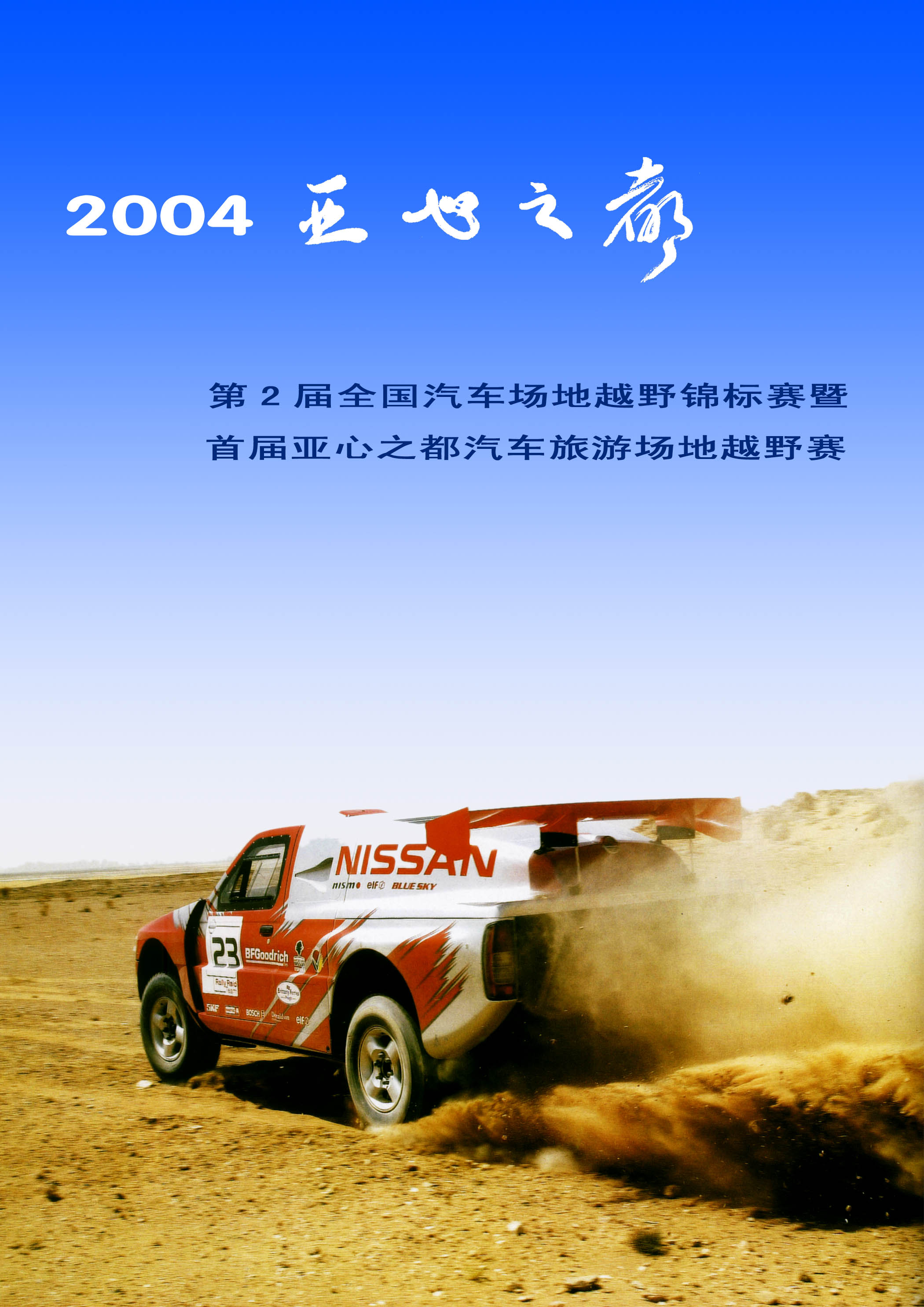一个迁徙的部落
——罗布人的前世今生
三毛
徜徉于罗布人村寨,似乎有了一种与大自然对话与原始风光肝胆相照的悠悠情思。尽管节假日旅游的人趋之若鹜,但它还是以一种旷世的宁静和超然,迎送来来往往的人群。这里没有唐诗宋词的古风,更没有名人和历代书法家的墨宝,有的只是这块土地的诉说和自言自语,沙土上生长着胡杨、红柳、芦苇,还有罗布人驱赶于荒漠的獣群,所幸文明之履的踏足又是那么的轻走漫步,总算保持了它特有的生态之美。村寨里仍住着一户名叫阿不都的罗布人家,还承袭着罗布人的传统生活习俗。我不知道古老的罗布人部落现在散落在何方?抑或民族的融合,罗布人早已改头换面过上了文明的幸福生活。但在这里,阿不都一家依靠海子,依靠景区的发展,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我敬畏这片土地和流淌于斯的塔里木河,没有它们的养育,罗布人也许就像1000多年前消失了的楼兰古城一样,早已埋葬在了肆虐的浩瀚大漠中。我也敬畏与罗布人共同生长的胡杨林和芦苇荡,是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才有了罗布人繁衍的庇护之所。
浩浩荡荡的芦苇不亢不卑的相互敬礼,狂风大作时只能匍匐高傲的头颅,潜行于根茎,等到来年的复苏。倘若深秋时节,在一阵金风的吹拂下,它那苗条婀娜的姿态又会给人一种以柔克刚的浓浓的暖意,也许芦苇本身就是风的使者,它的花絮,它的种子,在风的助力下轻烟曼舞,生生不息。
那么胡杨呢?乍看粗粝的树干,泥土色,如同干裂的龟田,但它的坚韧不拔让人景仰,“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抒写着生命的亘古绵长,同样也展示着生命的灿烂,金秋的胡杨,流光溢彩,就像一颗火热滚烫的心,点燃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指点着罗布人朝文明社会一步步迈进。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不能从历史的渊源中,确认罗布人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我只能从有限的知识和感性的认识里去寻找它的蛛丝马迹;我也不是考古学家,不能从挖掘的古迹碎片中判断罗布人的文明进程,我只能从零散的文字记载和臆想中去考究它的民风民俗。总之,罗布人是一个保持原始风味的部落,是一个神秘的部落,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与大自然抗争的勇敢部落。
称之为罗布人,大概是清朝末期才有这种称谓,再加之100多年前国外探险家蜂拥而至,怀着对西域无比的好奇,他们的探险考古总离不开罗布人做向导,他们把罗布人当成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荒原的“活地图”,罗布人这才引起世人注意并浮出水面。广义的解释,罗布人应该是生活在罗布泊一带的族群,随着罗布泊的干涸和自然条件的恶劣,以地域而命名的罗布人渐渐演变成一个漫漫长路中迁徙的部落。罗布泊因塔里木干河的改道和水势的强弩之末,早已失去往日容光,苍白枯竭得没有一滴眼泪,于是幻化成罗布荒漠,而罗布荒漠又要无奈的承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血盆大口的吞噬,大自然的残酷,说明了人定胜天的渺小。罗布人以本能的生存信念,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寻找,希望找到一块真正属于他们的绿洲,有水有树还有肥沃的土地。
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海子。
找到了海子(当地人称“海子”,其实就是塔里木河流域和塔里木干河在丰水季节漫过堤岸形成的池塘),就找到了罗布人赖以生存的基本元素,他们以捕鱼为生,制作“卡盆”(把胡杨树干挖空做成独木舟)打渔,用罗布麻捻成渔网,他们习惯了用大头鱼为主食,偶尔佐以捕猎的野生动物,至今还沿袭这种生活方式。清末《回疆志》记载罗布人“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捕鱼为食。”但塔里木河是一条季节河,枯水期在风吹日晒下,干流中下游的河水细若游丝而几乎干涸。丰水期,又摇身一变成为脱缰野马一泻千里,更是奔涌四溢的“乱河”。西周《山海经》有记载:“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盖乱河自西南注也。”文中所指“乱河“即塔里木河。面对它的反复无常,罗布人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一片片海子萎缩了,他们又用行走的力量去发现另一块绿洲,迁徙到有海子有胡杨有红柳有芦苇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统称的“阿布旦渔村”。“阿布旦”在罗布方言里意思是“水草丰美”的地方。罗布人就是以这种自然简单的生存方式维系着部落,乐观而随性。
罗布人操罗布方言,但没有文字。因逐水而居,远离红尘,他们更多了一份原始的质朴和率真的美。有考古学家和社会学家推断罗布人应该是曾经繁华的楼兰古都的后裔,可楼兰古都消失了1000多年,又没有确凿的文字史料描述,这里面出现的断层可能只言片语无法自圆其说,从同属罗布荒原地域的角度,倒也可展开丰富的联想。西汉以前,楼兰国就是36国之一,《汉书。西域记》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仟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楼兰城在西汉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中,各个民族各色人种聚集于此,一定发生了许多民族取长补短逐渐融合的动人故事,有一首《楼兰姑娘》旋律优美的歌,就是对那个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的古城的祭奠和怀想。我们只有站在幽幽的时空隧道感叹:曾经繁花似锦的楼兰古城,一夜间埋葬沙海,那些明眸皓齿的楼兰美女今何在?曾经骑着白马的王子又去了哪里?蓦然回首,难道就是眼前这些减衣缩食的罗布人吗?难道罗布人返璞归真又回到了世外桃源的原始生活?世上真有这样的轮回,或者说罗布人就是楼兰人的祖先,就是楼兰古城的原土著居民?这些谜团还是留给专家们去释疑吧。
所以,罗布人部落从某种角度谈不上文化底蕴的深厚,因为历史上曾出现的断层,没有文字的国度,迟早会被悄无声息地融入其它民族里面,他们的坚守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但罗布人对于文化的贡献不容小觑。在他们口口相传、口心相传的风俗民情中又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春风,正如为生计奔波而疲惫的所谓文明的都市人,却向往着回归大自然,在罗布人村寨这块净土上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喝最纯净的水,吃最营养的菜。罗布人的淳朴,罗布人对生活乐观的态度,罗布人发乎内心对自然的敬畏,也成就了罗布人民俗文化中最华丽的篇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用红柳串鱼胡杨炭火烧烤的罗布烤鱼,罗布人红柳羊肉串烧烤,是不可复制的美食文化。罗布人生性开朗,代代相传的独具一格的狮子舞已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他们用芦苇、用胡杨树搭建的草屋、树屋,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史上最环保的建筑。罗布人的长寿延年也在全国赫赫有名,被誉为“长寿之乡”,这都与他们良好的风俗习惯分不开。
同样,罗布人对于历史的贡献更是可圈可点。如果西域百年探险没有罗布人奥尔德克这个“活地图”的向导和引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也不可能发现“楼兰古城遗址”,或者说要推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可以说,罗布人的参与,开启了西域沙漠研究古丝绸之路上那一段历史谜团的大门,罗布人在罗布荒原的存在也成为了研究那段历史的“活化石”。
罗布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他们崇尚太阳,太阳就是部落的图腾。在“小河墓地”发现的太阳墓,尤其能看出这一带土著部落在生与死中对太阳的膜拜。太阳墓是世界上最奇特最神秘的土葬方式,用胡杨木围成七圈,呈太阳辐射状,气势宏伟。他们为什么信仰太阳,我也不得而知。但我相信罗布人一定是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好像是来自远古的神话,从天而降。他们行走于天地之间,热爱太阳,奉太阳为天神,相信天、地、人、神均能沟通,并显灵造福和庇佑子孙。
望着夕阳西下,天边一抹余霞静静地倒影于海子中,还有岸边的胡杨,我不想离去。当一只白鸥划过水面,我有许多话想说,但只有一句祝福:海子很美!停止迁徙的脚步吧,这儿才是你们温暖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