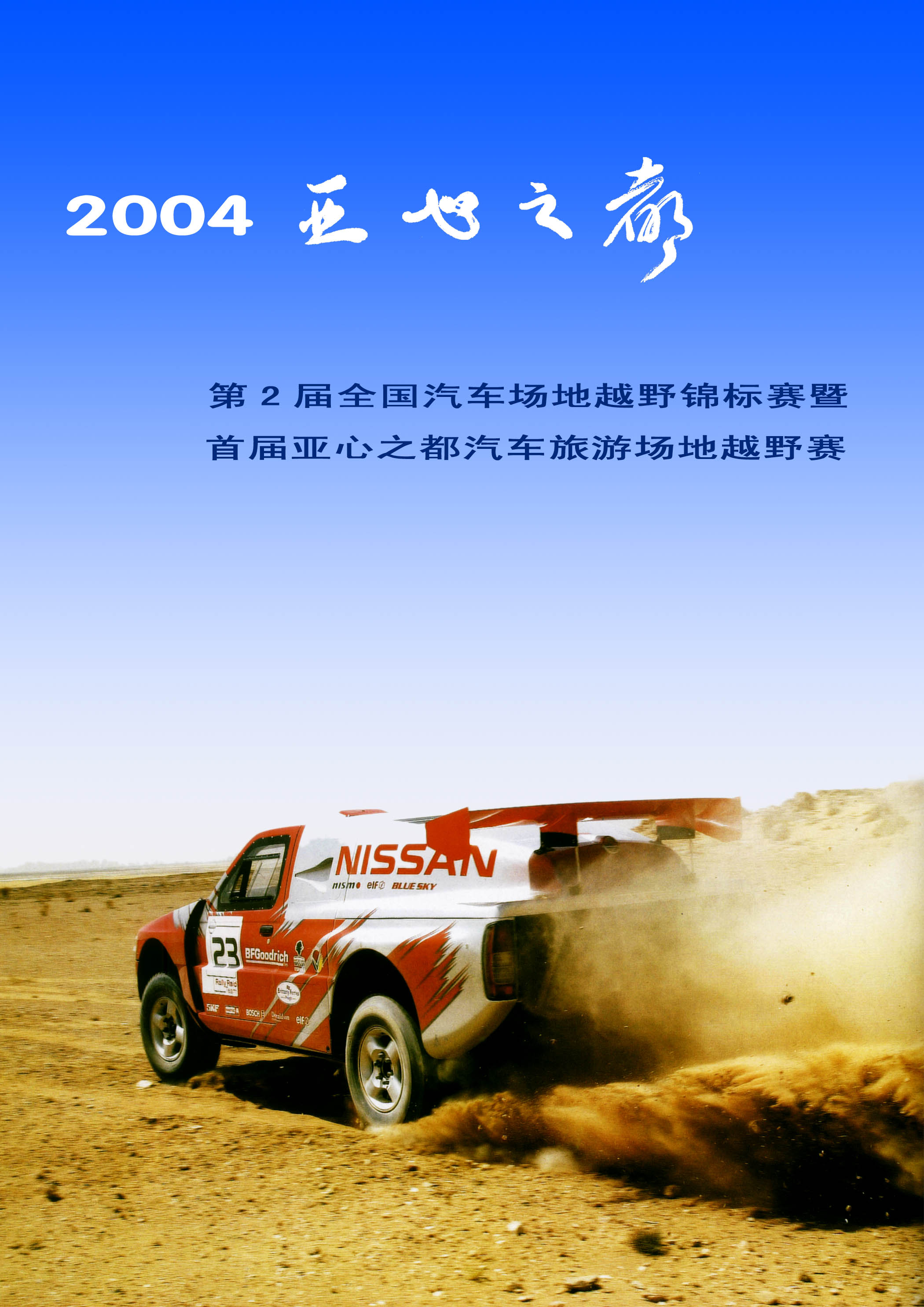平顶山村落的李氏夫妇
三毛/文
登上将近山顶的村落时,才知道,这也是七户人家。这万亩旱田的坪地、山坡、山顶,散落的村庄,大概都是以七户的基数来布局的,在平顶山万亩旱田壮观的气势下,出其不意地点缀着七八个若隐若现的小村落,也给这广袤的田海麦浪平添了几分人间烟火,雪峰之下,原野之中,“白云深处有人家”。
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妇,在屋前的小路上看着我们,当知道我们远游旅行至此时,立马露出了善意的微笑,男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红黑的面庞一看就是在万亩旱田的麦浪里翻滚了一辈子,女的扎着头巾,对我们的到来充满好奇。
人的这一生能熬过这相濡以沫平淡而孤独的日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守望麦田,依偎在热炕头,偶尔讲讲祖辈流落在这里的故事,一代一代默默相传,而平顶山就在他们这样的精心护佑下,才有了今天这般绝世美景。
同伴的两个年轻人被这美妙的景色吸引得滔滔不绝,而老汉乐呵呵地说:我们天天出门就是这样子,倒也习以为常了,你说它美它就美,但我们是靠着它来生存,过着我们村落的日日夜夜。
通过寒暄,我们知道了这对夫妇的家庭状况,现在仅剩两老留守在家里,一个女儿在乌鲁木齐打工生活,两个儿子就在木垒的县城安家落户,三个孙子、孙女也在县城的小学、幼儿园上学读书,村落没有学校,孙辈们在一个月之内由父母带着,上平顶山探望祖辈一次。
许多时候,陪伴他们的是120只羊,两头牛,一匹强壮的毛驴,还有屋前屋后四处觅食的活蹦乱跳的肥硕的公鸡、母鸡。这也乐得这对夫妇的悠闲自在。
扎着头巾的妇女指着菜园子周围的杏树、枣树说:到了夏末初秋两季,你们就能吃到新鲜的果子。然后热情地把我们请进屋内,一定要我们尝尝刚冰镇后的新鲜的酸奶。
这是有三间房的平顶屋,屋内很干净、清爽,一间宽若3米的炕床靠在墙边,炕上叠加着整整洁洁的棉被,一看就有一种融融的暖和。
在与老汉的闲谈中,才了解他是李氏家族的。两百多年前,他的祖先就从关内的甘肃省迁徙到了木垒,至今他们说话的尾音还略带甘肃方言的味道。李氏家族在历史上创造开辟了一个庞大的唐朝帝国,我不知道李渊、李世民父子是不是启蒙于甘肃,还是发迹于山西?但他们的血液里有西北汉子的粗犷和豪放,他们对领土寸土不让的雄心,使唐朝的版图扩充到了现在西域的各个角落。或许在冥冥的命运中,老汉已经接受了祖先的安排,扎根在了西域木垒的万亩旱田,在这里劳作、繁衍,并把这一方山水营造得井井有条,色彩斑斓,成为世人仰慕的旅游胜地。
老人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丰功伟绩,他们一直就过着简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生活,他们把村落看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因为这里面装着亲情,这里面还有血脉喷张的家族骄傲。
一碗碗洁白的酸奶端在我们面前,不忍浪费,一口喝了个底朝天。
我们这才觉得,在这里呆上一天,胜过城市的半个月。在这里你可以敞开心扉,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在草地里,躺在牛羊之间,看蓝蓝的天空飘浮的白云;在菜园子里锄草种菜,品尝自己的有机蔬菜;把山地摘来的野蘑菇,用细绳串起,挂在屋檐下,晒干晾干,然后抓一只坪地上觅食的老母鸡,亲自做一个蘑菇炖鸡的家常美味菜,然后把平顶山三眼泉泉水酿制的本地的糜子酒倒入杯中,醇香而甘冽,三朋四友围坐一席,这感觉在城里是无法相比的,因为这山野,这万亩旱田的大自然的芬芳,已经在我们的杯盘交错中,溢入我们的体内,也植入我们的心房。在美味佳肴的微醺中,几个人躺进温暖的热炕头,没有一丝杂念,蒙头睡到大天亮。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可我们是城里人,我们只能在这里短暂的停留。城市永远是一个没有底的欲望之都,回去了,再回到这质朴古旧的村落,也会“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扎着头巾的妇女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每隔一两年,当年曾在七户人家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要回到平顶山万亩旱田的地方住上一两个晚上。他们没有任何的奢望,有的全家倾巢出动,拖儿带女;有的孤身前来。看到平顶山如此大的变化,置身在万亩旱田的美景中,他们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是感叹曾经在这里度过青春的蹉跎岁月?还是回到大城市后再也没机会体味到这原始的风味?也许什么都有,五味杂陈。
他们这一两天的生活,就是睡暖和的热炕头,吃菜园子的有机菜,然后尽情地在他们熟悉而陌生的平顶山万亩旱田和草地上撒野。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战斗,每一次的到来,既是旅行者的重游,又是一种人到中年的心灵回归。
平顶山的村落生活,可以变得更丰富。
城市空虚无聊的日子也可以在村落里得到净化。多放一张桌子,多摆一双碗筷,多增加一床炕,这样的旅行,自驾也好,民宿也好,而这种切实的体验,也算是对乡村生活的一种真正的认同。
很不想离去,但不得不告辞。新鲜的酸奶味还在喉结蠕动,热炕上的热量还储藏在体内,那两张热情和善的脸还在眼瞳久久不能散去。